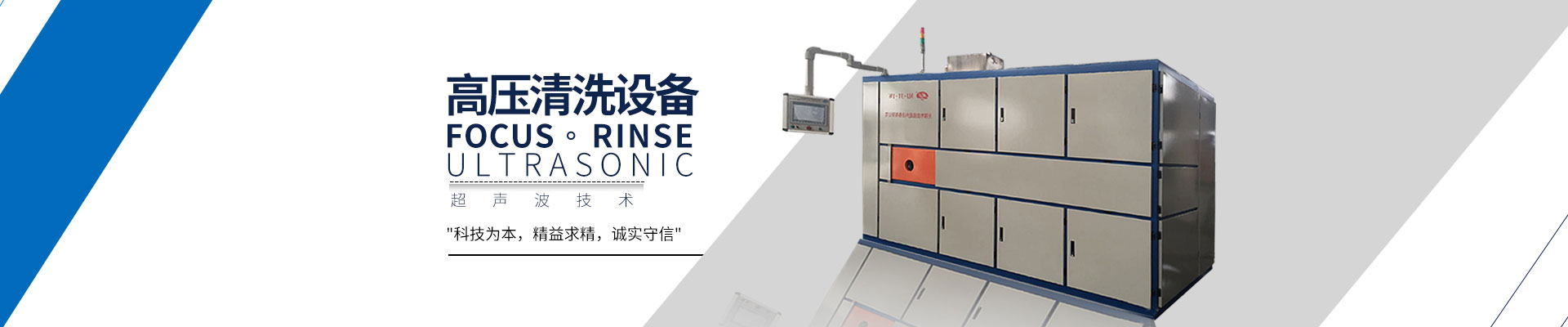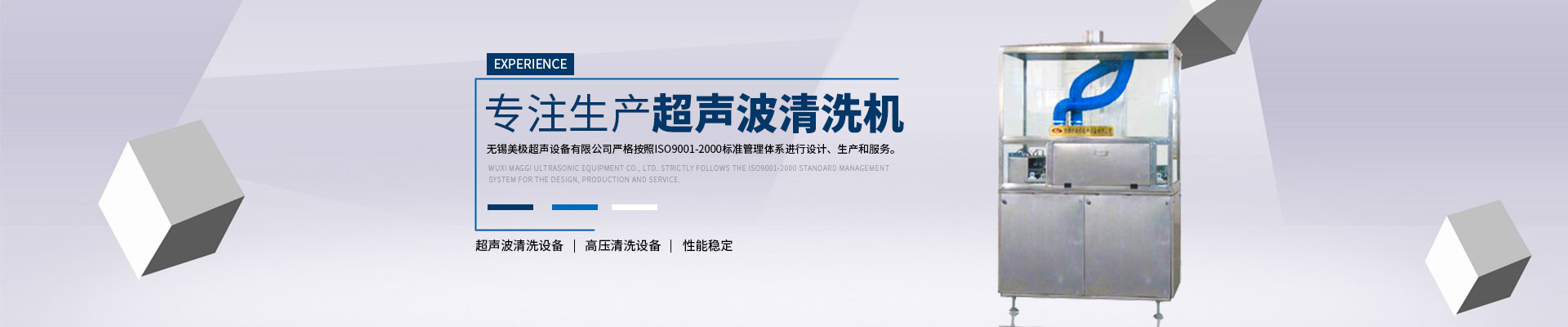中关村从1980年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创办以来,发展了30年,历史沉淀和科学技术基础在中国无出其右者。站在历史铺垫的高度之上,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示范区核心区面临着两种发展模式之选:自然增长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四通集团原总裁、华志泰欧企业管理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说:“如果要实现示范区的目标,一定要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方式;而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要在几个点上实现重大突破。那么现在必须研究突破点在哪里?”
关于中关村的发展,有很多困惑。其中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中关村发展了30年,为什么形成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和品牌少之又少?企业规模化发展走入困局,又将如何破局呢?朱希铎断言,“以中关村现有的企业家单打独斗、个人奋斗的方式肯定做不大,没办法实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目标,企业只能走联合、集聚的道路,共同做大。这就需要更为高瞻远瞩的领军人物,但是中关村绝大多数企业家,都跨不出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企业也难以让别人跨进来。所以,企业仍然只能依靠自我滚动发展。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寄希望于从中找出一个苗子,政府好好支持一把,就能长出一个千亿元规模的企业。、如果将来做强做大是需要跨企业、跨业态、跨资源板块的集聚的话,首先是中关村企业家要跨出自我封闭的文化界限,这是十分艰难的。所以,我认为,创业文化和中关村自以为是的创新文化,是中关村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最大障碍。”
2001年时,记者曾经采访中关村一家医疗器械行业的企业,当时企业成立约10年,年收入在2000万元左右。公司的掌舵者是一位技术人员,他们选择的方向,有效地将国外医疗器械垄断的市场打破,成功将产品售价大幅度降低。为了取信于医院,在国外产品一统天下的市场中撕开裂缝,企业与医院做了长达两年的跟踪与合作,终于打开了市场。
2010年,记者再次采访这家企业,企业的规模仍就保持着10年前的水平,原有产品占有了国内大部分市场,但是没有继续的产品创新,企业在近20年的时间里,无显著的发展。
这在中关村里并非特殊现象,这类企业有一个名字“小老树”。当我们对于中关村这样的现象几乎习以为常的时候,却缺乏对这种现象针对性的研究并提出具有有效价值的解决之道。
言及这样的一个问题,政府困惑,企业也困惑,可是究竟困惑什么?是困惑企业为什么做不大,还是企业如何做大?是困惑政府该怎么样支持企业,还是企业该怎么样自强?就连困惑什么样的问题本身也是困惑。十几二十年来,“小老树”现象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中关村的发展,依然没有消除。
在朱希铎看来,虽然中关村从始至终坚持创新,由此带来的总收入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加,但是,创新的效率和效果却难说差强如意。这其实就是因为中关村很多企业对创新的认识存在局限性,重视专利数量,却忽略了整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也就是说,缺乏可持续创新的基础。
1992年,朱希铎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谈及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时就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外高科技企业有骨骼性差异,并不是简单是头发颜色、眼睛颜色的差异。骨骼性差异是什么概念?看一个企业的成本链构成,我们是在低人力资源成本、低市场营销成本、低研发技术成本、造成本、低服务成本、高资金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了低利润率运行;IBM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正好相反,他们是在高人力资源成本、高市场营销成本、高研发技术成本、高制造成本、高服务成本、低资金成本的情况下,实现了高利润率运行。成本链相当于人的骨架,人家是脖子、腰、腿、胳膊都长,所以个子高;咱们是全短,所以个子矮。那么现在企业能不能拉长一段,比如脖子,实际上不可能拉长,因为形不成那样循环的结构。”
朱希铎认为,技术创新体系中,专利只是其中一个内容,还包括研发投入的体量,研发投入与盈利回报的关系等。“美国大公司,就是因为研发有极大的核心竞争力,造成产品在市场上有极大竞争力,以及极高的回报率。这里所说的研发投入和我们大多数企业所理解的研发投入不同,研发体系投入和有没有研发、有没有研发投入是两码事。比如在英特尔和微软,最前端的研发,是一帮薪酬最高的大师级发明家,他们每年对公司不承担任何研发任务,企业营造一个条件和氛围,寄希望于他们偶发的一个发明火花,也许就预示着全球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点,一旦企业抓住这个契机,转瞬就价值连城。整体研发体系中,一定有人研究10年后的技术,有人研究5年后的技术,有人研究3年后的,有人研究现在的技术产品,它是一个完整的研发体系。不同层面的研发都需要投入,这样才可以源源不断地保证企业的创新发展。企业研究10年后的技术肯定不是一个具体的产品,而是主流产品未来发展的最核心的技术,这样才可以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放眼中关村更多技术着眼于产品本身的微调整,咱们大部分专利都是改变产品外形,或是一些基本功能的调整,所以到不了世界量级的技术创新。这就是中关村创新乏力、企业长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希铎说。
对公司为何长不大,作为企业的掌舵者,在其位理应谋其事,但是,往往一叶障目,对于企业做不大,他们存在思维上的局限性。
陈庆振在掌舵中关村当年叱咤风云的科海时,也不曾意识到其中问题的关键。如今,作为中国民协秘书长,陈庆振每年至少要到全国各地跑一趟,而且每次必然深入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的需求和问题,“我发现了一个无形的束缚。”陈庆振说,“中关村很多好技术,企业却做不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是科学家、工程师,能研发出产品,但是,如何将设计批量生产、上市,以及管理公司、筹措资金都是短板,却什么都管。”他看到了太多的案例,那些卖出去的技术往往做得很大,而掌握在企业手中的却丧失了做大的机会。科海曾做出中国第一部汉字处理装置,但是汉卡却成就了联想;科海做出中国第一部超声波加湿器,当年市场销路很好,但各位明白亚都不曾知道科海是这项产品的鼻祖。
按照陈庆振的说法,企业领导者所存在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而且,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成败的关键不在于长板而往往取决于短板有多短。这也印证了多年前记者正常采访紫光股份总裁李志强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缺钱的企业很多,但是只缺钱的企业却很少。团队尤其是掌舵者的综合素养存在明显缺失。
之所以企业不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是因为当局者迷,另外,陈庆振认为,“很多企业的技术不错,市场对此有需求,因此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企业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的自信心就膨胀起来。创始人永远牢牢控制着企业的所有权,致使公司发展缓慢,做不大。”
对此,朱希铎深表赞同,“中关村企业的特点,就是有很重的企业家个人色彩,但是企业家色彩,在新的时期,是对企业再发展、上台阶有严重阻碍。中关村有一些企业,已发展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比如做到1亿元的规模,企业家的目标是要做成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不知道之所以企业做不到百亿元规模,最大的障碍正是他自己。创业者会因为成功创业而膨胀,觉得自身什么都懂。但实际上,未来企业怎么发展,资本问题、现代营销问题、产业链问题、国际化问题、人才问题、管理问题等现代企业所要解决的大规模发展的很多问题上,创业者大部分都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往往还是企业的掌舵者,导致企业难以跨上规模的台阶。”
“再过10年,中关村还像今天这样是一大堆小企业,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不符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定位和发展要求。那么企业怎么做大?你看硅谷,硅谷是一帮科学技术人员创业创新,大量风投等待,见机就投。硅谷深层次产业化转移的文化在支撑,所有的创业者在创业成功之后,就琢磨着卖掉。卖了之后,要么继续在大公司搞研发,要么继续开发新的方向。但是中关村很少有创新成果就为了卖出去,研发出来企业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掌控着。想到中关村投资的风投很多,为什么落不下去?你看看中关村风险投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实际上看的企业和项目都很多,落不下去的大部分原因是团队甚至企业家不行。往往企业研发的方向很好,产品技术不错,但是,最后谈来谈去还是不行。中关村大多数创业者企业家过分注重产品和技术层面的问题,缺乏企业家的职业素质。”朱希铎说。
朱希铎强烈建议中关村企业家好好研究研究柳传志,“联想的技术开发并不是他主导,但是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中关村需要一批能够驾驭百亿、千亿元规模企业的领军人物,这相当于是一批高水平、世界级的企业家。企业家并不全是创业家,也并不全是科学家,可是现在中关村的企业家,基本上既是创业者,又是发明家、工程师,还是企业家,角色全混一块儿了,靠他去营造一个规模化、产业化的体系,他没那个心胸,也没那个驾驭能力。”
中关村发展集团董事长、原海淀区副区长于军在中关村园区成立20年的时候曾说过,中关村的潜力仍没有完全释放,知识经济、新经济只是初步形成,在公司数、人数、资本、资源的对接上,与那个1000平方公里狭长地带的硅谷相比较而言,20年只是一个序曲。
由此能够准确的看出,对于中关村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回避。那么如何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并实现中关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迫切地需要研究的命题。
大唐是TD产业标准的提出者、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也是标准技术的指导者。作为中国自己的3G标准TD-SCDMA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国外标准15年的道路。原大唐移动总裁谢永斌感触最深的就是搭建产业联盟,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大部分技术处于分散状态,光靠一家是不行的。大唐有义务推动国内整个产业联盟,把国内的有名的公司纳入产业联盟。开放了1010份文档,组织了相关讲解,为推动产业、使产业从所有的环节同步起飞,大唐做了巨大的努力。成立产业联盟后,各环节企业明确自己的分工与合作,经过5年的整合,TD逐步建立,完善了从职能网、核心网、测试环境、测试仪器仪表等完整的产业链,保障了TD的有序发展。多年的竞争对手,变成了互动的合作模式。”
产品创新让中关村迈上第一个台阶,企业创新则带领中关村迈上第二个台阶,“中关村的第三个台阶,应该是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企业创新有很大区别,不是一个小企业研发个产品,卖10亿20亿元。产业创新都谈论什么文章呢?比如产业链、产品链、资本链、人才链、市场链变成是一种很规划化、很国际化、很市场化的集群,才能称之为产业创新。”朱希铎说。
他认为,国家给第三阶段的中关村两个词:一个是“示范区”,中关村必须有示范作用,而且是向全国甚至全世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一个是“先行先试”。这其实就是给中关村出了一道题,也是一个授权。如果中关村做得好,其他区域又没有做过,那么就先行先试;但是,这也出了道题,就是中关村必须交出一份答卷,到底先行了什么,先试了什么,“我很赞成十百千工程,但是现在非常需要从解读十百千的定义、条件、计划以及十百千之路来理清脉络。现在十百千工程没有时间表,没有提出比如在十二五期间或者10年规划,出多少个千亿级企业、多少个百亿规模的企业、多少个十亿元规模的企业。为什么不敢定这个目标呢?主要是因为大家没有对十百千这个口号进行充分的解读。如果不进行解读,就想不明白下一个阶段示范区建设应该往哪儿发力,出台政策往哪儿出。”
产业创新的特征是什么?一是规模化,二是国际化,三是市场化,而且是非常充分的。充分的产业化创新,支撑条件是什么?技术创新、高品质人才、资本杠杆。
然而,朱希铎认为,中关村支撑产业创新的3个条件都存在很明显的不足,而这也正是中关村许多企业没办法做大的原因。先看技术创新,朱希铎曾算过四通R&D占企业营收的比例,连1%都不到。他去美国考察,IBM、HP这一些企业R&D的投入比例占到出售的收益的8%~10%。当时IBM一年的收入是400亿美元,那么,其R&D投入就是32亿美元。而且,这个比例并不是简单的R&D投入除以出售的收益,而是整个公司的运营体制就基于这样一种成本链,在保证每年拿出8%的R&D投入的情况下,公司一直能够良性运转并保持一定的利润。其次看人才支撑,上文提到的领军人物的缺失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再看资本支撑。大规模企业的运作,必须是有大规模的资本支撑。比如日本索尼、松下、日立等企业,银行都是股东,背后都是大的财团在支持。“以中关村现实条件来说,产业创新的条件还差得很远。但是现在危险在于,大家都没觉得差多远。大家都感觉再一努力,中关村明年就更好了,后年就实现目标了。但是,完成什么了?达到什么目标了?仅仅是总收入的增加,这不行!”朱希铎说。
“现在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做出那么多大个儿的?有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政府在跨企业单元进行配置和组合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在跨企业单元边界的资源配置、资本集聚、产业链集成上,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朱希铎说。
企业要实现跨企业边界的发展,实现产业协同创新,要突破的障碍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局限,体制和政策的创新至关重要。这也再次体现了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必须先行先试的重要意义。然而,朱希铎的现实遭遇,却让他感到诸多无奈。
2010年11月初的一天,朱希铎正在看中关村“十二五”规划的文件,“支持产业业态创新,鼓励支持以重点项目为纽带、集若干企业和研发机构合起来的联合体”的内容再次被提及,深深触动了他。这样的项目联合体,2009年时朱希铎一口气攒了9个,章程写了,项目报告也写了,却发现没地儿挂牌。尽管海淀区领导也主张支持建立几个大联盟,大联盟底下再设立几个小联盟,但是,政府同样解决不了挂牌问题,因为法律上没有处理方法。朱希铎去民政部,发现联盟的组织形式和社团法人不一样,它是一个项目联合体,不在乎行业及公司数的多少。民政部有关人员说:“如果我把这个牌子给你了,这个行业的别的企业怎么办?”但若注册行业联盟,就做不成项目了,这是一对矛盾。“从政策层面来看,新型产业化组织,支持;先行先试,支持;以重大产业化项目为纽带的联合体,也支持。但是,差一步,再走就走不下去了。很多政府的想法,在执行层面就会遇上问题。”朱希铎说。
2010年初,中关村管委会开会讨论先行先试的项目意见,朱希铎当场表态,“现在先行先试的意见写得很全,涉及了方方面面,但没重大突破;既然让咱们先行先试,我就说两个现实问题:喊了很久要成立中关村科技银行,没人批;大项目联盟,没有地方注册。如果管委会能发一个文件,比如授权服务体系建设处为项目联合体的组织单位,只要管委会能够批了,我拿着批文就可以到民政部去登记备案就行了。现在政策只说了后一半,就是大力度给予各个联合体项目和支持,但是,前提是,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法的联合体,这是个问题。我攒了这么多联合体,没地儿领证儿去。联合体有章程,包括怎么运行项目、怎么承担相应的责任、怎么共同投入,都有详细的规定。但是,所有的改革都卡住了。”眼下,组织项目联盟已逝去两年了,朱希铎却没有使当初对企业所做的承诺变成现实,“联盟也不找我了,这真的是很令我苦恼。”
作为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负责中关村开放实验室4年了。2009年他提了一个建议,支持、培育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研究院。第一,产业创新研究院是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不是某一个单独企业的,有跟这个主体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是个小的企业集群;第二,由北京民协来促成与这个产业研究方面相关的实验室,与他们变成一体的关系,组建若干产业研究院。此后,一些行业领头企业积极做出响应,尹卫东成立了科兴生物疫苗产业研究院;秦升益成立了自己的仁创砂产业研究院;王小兰也成立了一个时代焊接技术创新研究院然而,这项工作也不了了之了。
“我努力推进,但是实际上却推不动。”朱希铎的无奈不是他个人的无奈,是中关村发展当务之急的微观反映: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可能比技术创新来得更重要。
如何破局?怎么来实现创新发展?朱希铎认为,如果中关村不能在创新的方向上把问题想明白,并且提出策略性的发展规划,对于中关村未来的发展,他将会感到很悲观、很有危机感。
虽然中关村在2008年实现1万亿元的技工贸总收入之后,这一个数字今年再度增加至1.5万亿元,但是,数据背后企业和区域的发展任旧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没办法忽视。中关村企业做不大的原因,朱希铎认为要从几个维度分析,因为界定中关村历史的特点,一是看技术创新、二是看企业、三是看企业家、四是看政府、五是看政策。
中关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企业家就是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当时,只要敢蹦出来下海就行,然后成立个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公司。当时是什么人跳出来?都是一群不甘寂寞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单位有研究背景,但是思想又很活跃。
中关村企业做什么?就是做产品、卖产品,只要做一个产品,就成就一个企业。
政府做什么?政府天天跟着企业跑,到企业了解问题、处理问题。当时,政府就为了帮助下海的企业创新,支持、帮助、解决困难。
政府的形态是“试验区办公室”,企业的形态是“两通两海”,文化是“四自原则”,这是一种解放,一种改革开放中跳出旧体制的一种解放。
中关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企业家都在干什么?都在做大做强,多元化发展,都在喊着“二次创业”的口号。
企业做什么?投资建工厂的、搞中外合资的、上市的,几乎大公司集团都在做这些事情。
政策做什么?中关村出台了第一个地方政府制定的带有法律性质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配合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有很多突破性的条款,破了几个界限,给了公司能够做更多事情的空间。
在朱希铎看来,当中关村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5个要素变得混沌起来。在发展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示范区核心区的新的历史背景之下,初步开始的探索尚未解决所有的困惑。
不可否认,政府需要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来创造一个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毋庸置疑,企业要审视自身,从成功的创业中找到失败的教训和发展的短板,实现可持续的创新和可持续的发展。但是,我们更需要理清,中关村的发展缺什么,企业的创新少什么?创新的方向、方式和路径是怎样的?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上,怎么来实现有效的突破和创新?匹配今日中关村发展的文化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
在中关村成绩单的背面,是一堆长长的问题,开年之际,中关村需要将已取得的成绩放下,认真去解决一个个发展的问题,也许很难,也许很久,但是,在解题的路上也许会遭遇破题的顿悟,而沿着既定的道路低头前行,却可能距离伟大的目标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