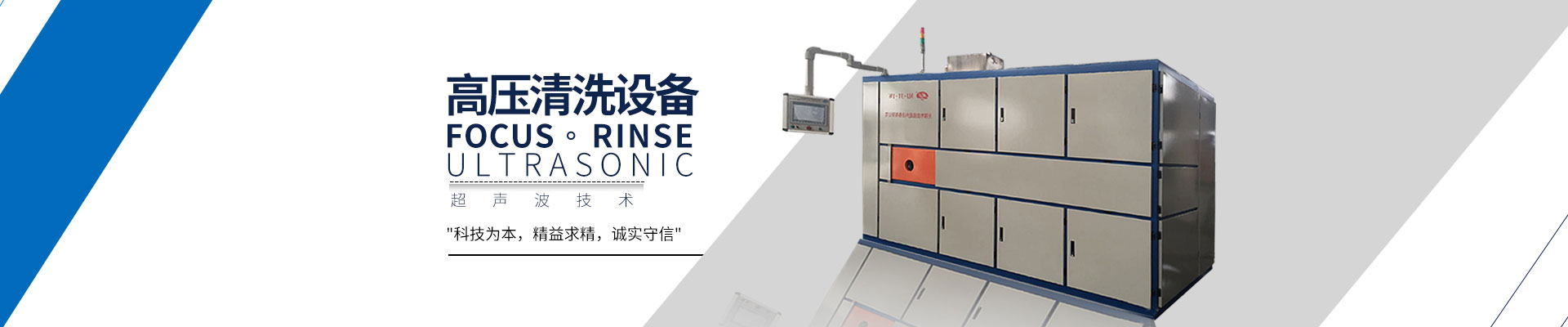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经121岁。作为惟一没有同打过仗,惟一敢对、蒋介石多次直谏的高级将领,
父亲一生与、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父亲长期置身于最高决策层。
但是,虽然跟随蒋介石20年,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周恩来等中国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建国后,他曾有短暂的喜悦,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
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这么休息过了。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
“拿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的总裁,我是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
而他在,在主战,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更跑到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4月到6月,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我是一个党员,但现在站到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啥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
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曾经有过判断。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这个计较……”
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
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的祖国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就是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父亲最后想通了,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理论上的——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就想通了。”
父亲自问,应该是个怎样的党?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他所憧憬的的灵魂哪里去了?
他所追求的“恢复革命精神,实行民主政策”,为的是把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但是却回天乏术。
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人的面,指了指父亲说:
“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
“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相关声明之日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啥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常念念不忘这两句线月,政协会议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父亲在世时常讲,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
每次开会时,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不发言的时候少,实际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是,父亲也应邀参加。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父亲,对他说,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父亲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还说,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只要父亲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立即给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打了电报,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要他们正式公开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那时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
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经过反复思考,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尔汉。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
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父亲接信后第二天,又致电陶、包,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要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不应再犹豫顾虑。
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到北平后,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父亲曾经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
到了那里,傅先生问借多少,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
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一星期后,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然后写道:“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
后来,毛主席由马鞍山去南京视察,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江渭清:
1951年,根治淮河工程开始,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到工地进行视察和慰问。
得知父亲病了以后,在5月5日特派持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1952年夏,父亲从西安到北京,来到家中,长谈了两个小时。父亲说:
毛主席啊,我们的祖国这么大、这么多人口,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搞贸易,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
1958年5月,反斗争接近尾声,父亲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
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
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一种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但是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里怎么未提及?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父亲陪同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路上,他写了4万多字的日记。这一年,父亲与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
这次视察是邀请父亲去的,他很珍惜这次机会,每天的视察和与的谈话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
回来以后,父亲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诚的、热烈的爱戴之情,以及毛主席热爱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
父亲曾经回忆说,毛主席在这次视察时曾谈起父亲的世界观问题。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
“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没解决,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他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满足过。
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超越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要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1958)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不理解,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
、周伯伯知道后,保护了父亲,批评某些人“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1966年初夏,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运动,全国乱翻了天。学生不上课了,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毛主席在城楼上多次接见。
每年6月至7月,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我尚未动身,来抄家了。
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声称是来破“四旧”的。
我家是一座旧楼房,大儿子正好在家,立即开了门,他们一哄而入,楼上楼下乱窜。
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一些衣物、首饰,他们翻箱倒柜,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我让他们贴上封条,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
过了几天,另外一批又来了,坚决要把上批封存的东西拿走。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心中很不耐烦,直摇头。
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凶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次日返京。
砸了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佩剑,还责问为啥不挂毛和语录,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扬长而去。
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语录。
其实,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水利部了,可是这次要在我家找。
那么大一辆车,何处能藏?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这不是没有常识吗?都是高中学生了!
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人声嘈杂,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我们一定要下楼为之开门。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
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
来抄了多次家,《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
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了。”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
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把煤卸下,身上汗流浃背。
“我的长子远在台湾,长婿如长子,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如仍有问题,再叫他回去,可以吗?”
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后派来接管了,就进不来了。
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他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开始后,很多老干部靠边站,父亲想不通。陈毅亲自来劝他说:“这是群众运动嘛,没关系的。”不久,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在城楼见到。问“去你家了没有”。
听了这话,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
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问起外面的情况,素德如实相告。父亲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不好,眉头深皱,他对名为破“四旧”、实则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摇摇头说:“若干年后,这将是个大笑话。”
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当他听说除了有“打倒”之外还出现了“打倒朱德、陈毅”等大字报时,说:“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
情况越来越糟,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拉出去游街示众,甚至被逼死,一些派人士也受到冲击,父亲心情沉重。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他主要是长期对不理解。他心情很不愉快。他没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
父亲生病期间,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平时,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有时还请我们全家。
父亲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总理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总理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听说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
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不会反对您老人家。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解放后也在西北。他对彭德怀很了解。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父亲担任副主席。
这封“”寄到了周伯伯手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
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
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当时其实不理解为啥不送信给。“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面见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他还说,“我一定去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在检阅。父亲执意要见,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后他说:
“主席啊,你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
“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你怎么办呢?”
父亲也站起来了,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但是站起来后,父亲并没有说话,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很沉闷,没有说话。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但他闷闷不乐。
的地位慢慢的升高,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父亲忧心忡忡,而周伯伯处之泰然。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